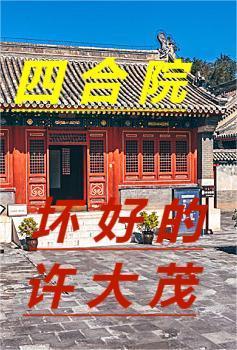小說村>眉目如畫+番外 > 第38頁(第1頁)
第38頁(第1頁)
「若是當初她殺了他,就不會這樣。啧,真可憐。」當年如果殷鑒死了,威名赫赫的白虎神君亦不過是她手下一員敗将,渺小不值一提。可他卻還活着,千年來唯一一次失敗,足以讓心高氣傲的女子銘記一生,從而日思夜想,從而時刻期盼,從而心中眼中滿世界滿天下唯剩殷鑒一個名字。「我和她是雙生姐弟,從小她就這樣。」楚眸又靠回了牆,銀色的腰帶箍出細細一截腰,雙眸如含天地之光。幾乎與自己同時誕下的姐姐自小寡言,對修行有着天生的異禀與執着,妖者總有一處偏執,為名、為利、為情,好童子、好妙女、好一顆鮮活亂蹦的心。她隻為殺,好刀尖下一張張絕望畏懼的面孔與撲面而來的那一陣溫血。所以她可以弑殺同族長老,手起刀落,幹脆不帶半點猶疑;可以浴血屠城,殘破的屍身堆積如山,她端坐頂峰,如身處蓮台;亦可以為了殺死被奉為戰神的白虎神君而乖乖偎進他的懷裡。隻要為了殺,做什麼都可以。刀劍在手的她城府深厚不擇手段,一旦放下屠刀,便隻是一尊會走路的娃娃。自來隻有他伴着她,從出生至叛逃至悖逆了天下。「我喜歡她,自小就喜歡。」連說這話時,他也是一副詭異的笑臉,嘴角上翹的弧度妖異而漠然,「她是為殺而生,我生而就是為了照顧她。否則,世間早已不存楚耀之名。」微紅的火星在劈啪作響的柴火間跳躍,沸騰的湯水在鍋裡「咕咕」作響。殺意升騰的蛇将蒼白的手舉在眼前仔細觀瞧,細長成一線的眼危險地瞇起:「當初殷鑒為什麼不死呢?他死了,她就不會記得他了。」他長身而起,殺意自眼中溢出,雙手攏進袖中不願再拖延:「若是殺了你,你說,他會不會心疼?」典漆不躲不閃,站在竈前,手裡還端着方才的鹽罐。伶俐的灰鼠歪着頭認真思索,半晌,露出一個無辜的笑:「這個……我也不知道啊。」楚眸上前,自袖中抽出的雙手蒼白近乎透明。他冷哼一聲,墨綠色的眼瞳暗沉如雷雨前的天空,灰鼠細細的脖子輕易被他握于掌中,脆弱彷佛一折即碎:「等你死了,便知道了。」「那麻煩你到時告訴我一聲。」呼吸有些困難,典漆厚着臉皮同他說笑,眼珠子「咕噜」又一轉,話題随之而變,「若是楚腰死了,你怎麼辦?」「若死的是殷鑒呢?」因為脖頸被束縛而被迫高高仰起頭,灰鼠眨眨眼:「找個更好的。」臉色陰寒的蛇因而滿臉興味:「是嗎?」典漆沒回答,張大嘴努力地喘氣。有人站在門外道:「真叫我傷心。」艱難地扭過脖子循聲望去,一襲不沾半點凡塵的白,一汪天湖般澄澈的藍。帶着銀冠的男人潇潇灑灑立在門檻外,發冠齊整,衣擺幹淨,彷佛隻是出門去往花街柳巷轉了一圈,風采翩翩依舊,眉目間更添幾分飛揚。「我隻道你跟你的舊相好跑了,唔……」灰鼠尚有力氣嘲弄他,話說到一半,即被狠狠扼住了喉嚨再難開口。楚眸牢牢捉着掙紮不休的灰鼠不松手,雙眼恨恨看向來人:「你來晚了。」殷鑒跨進屋,潔白的衣擺擦過青色的闆磚發出「沙沙」的輕響:「你不問她的下落嗎?」「呵……」神色鎮靜的蛇妖隻是笑,手中施力,有意讓面前的男人看見少年泛白的臉龐,「這還用問嗎?她若能光明正大勝你,當年又何必刻意接近?」「說得也是。」神君颔首,不知不覺,又再靠近一步,「當年是我疏忽了。」他不領情,挾住灰鼠随之後退:「彼此彼此。終究讓你逃了,這也是我們的疏忽。」殷鑒搖着頭歎息:「你不去見她最後一面?」他卻理所當然:「沒什麼好見的。等等我倒是更想看看你會是什麼表情。」話音方落,典漆就覺一陣痛楚,喉頭彷佛要被生生折斷般難受:「唔……」想要開口卻吐不出任何詞句,模糊不清的視線裡隻有男人不斷靠近的身影。「他若死了……」他的眼睛始終盯着楚眸的臉,明明是一般的身高,卻讓狠戾的妖生生産出一種幻覺,彷佛自身渺小如塵埃,無時無刻不在他的俯視之下,聽他在耳邊一字一頓沉聲叙述,「你道本君能輕易放過你?」楚眸說:「我本就不打算活着走。」殷鑒輕聲反問:「是嗎?」
請勿開啟浏覽器閱讀模式,否則将導緻章節内容缺失及無法閱讀下一章。
相鄰推薦:亂臣+番外 竹報平安 不正常關系+番外 你明明就是喜歡我+番外 獨家虐戀+番外 颠公颠婆們,請清醒一點 庸君+番外 微臣+番外 不犯錯的法師 重生穿越:最強融合系統 穿回古代搞刑偵 降魔塔 賀新郎+番外 那些風花雪月+番外 思凡+番外 贅婿狂飙,被退婚的我無敵了! 四合院:我的妻子實在太争氣了 被分手後,男頂流天天糾纏求複合 他的獨寵+番外 六零:小妹她又萌又飒